读嘉
独家视角 读嘉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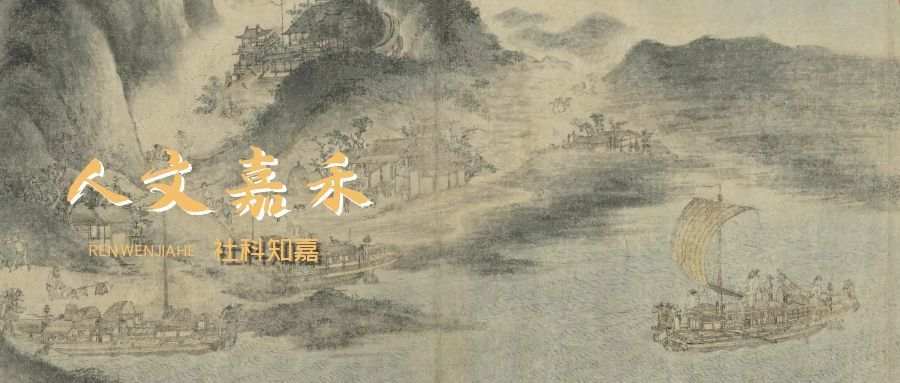
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东临大海、南倚钱塘的嘉兴,在每个与浪花追逐的日子里,向海而立。
风从海上来,将一个个海洋文化的印记写入城市的记忆,刻入文明的根脉。
舟来舟往,冬去夏归,红楼出乍浦,开启世界之旅;“海舶辐辏,岛夷为市”的海港,汇百川之巨贾;“筑室招商,世揽利权”的航海世家,扬帆于海上。
潮起潮落,日出日落,先贤追逐海洋的脚步越走越远,文明的触角越伸越广,链接着江海的往来,中华文化随着浪花,跨越重洋,播向八方。
今辑录嘉兴历史上的精彩出海故事若干,看嘉兴海港的风云、嘉兴航海的辉煌。
红楼出乍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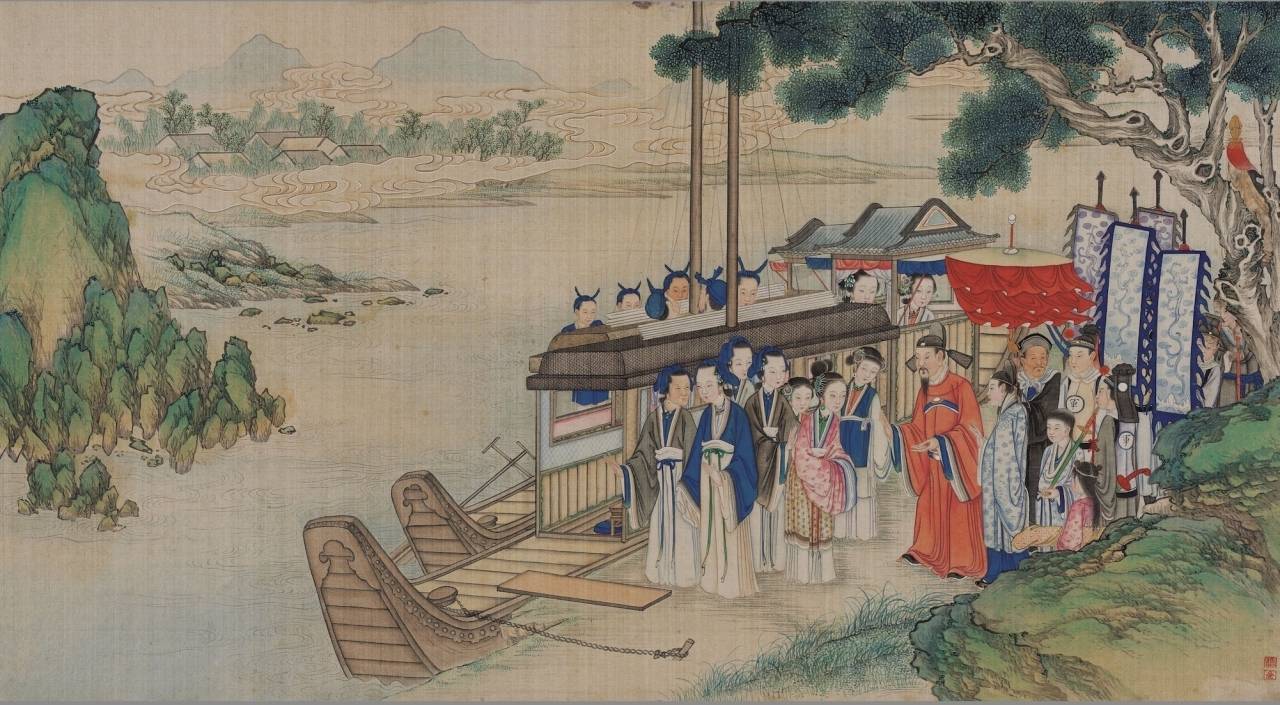
清 孙温 红楼梦图册 旅顺博物馆
230年前,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一月二十三日,熙来攘往的乍浦港,一艘满载货物的南京商船,告别送行的人们,扬帆起航。
目的地是日本长崎港,船主人是南京商人王开泰。经过16天的海上航行,终于在十二月九日抵达。
寒风凛冽,港口却是热火朝天。各式货物一件件被转运,最特别的是一箱箱书册,在76种书籍中就有《红楼梦》九部十八函,几乎可以想象,当地读书人定是如获至宝。
这份长崎村上家族保存的“差出账”古文书是迄今《红楼梦》出海最早的确切记载。
堪比中华“文学昆仑”的《红楼梦》首次走出国门,开启它的世界之旅。随后,《红楼梦》流传到朝鲜、越南、泰国、缅甸、新加坡等亚洲国家,19世纪开始传播到西方。
可以说,《红楼梦》出海是中华文化出海的成功范例,与世界共享文化成果,中国的探索早已有之。
很难想象,在中日都闭关锁国的情况下,程甲本在国内才排印两年,日本也开启了“红楼”的“木石”奇缘。
当时,因中日都不允许日本人来华,从事中日贸易的主要是中国人。
康熙六年(1667),清廷特批乍浦港为与日本的通商口岸,用以采购日本的铜,同时,银、海带等海产品被中国商人漂洋过海,从日本长崎带回乍浦,又将生丝、绸缎、药材、茶、糖以及书籍和文房四宝等送达长崎。所以,有红学家指出,那些《红楼梦》里看到的大观园中的舶来品,可能就是乍浦转运的。

红楼别浦
彼时,中外文化交流随着海浪往返频仍,大批中国文化典籍进入日本市场。
1793年冬,与《红楼梦》同船出海的76种书籍中,有平湖人高士奇的《消夏录》、桐乡人张履祥的《张杨园集》、乍浦人沈筠的《乍浦集咏》等乍浦及周边城市的文人之作。
嘉庆八年(1803)“亥七号”又带着两部各四套《绣像红楼梦袖珍》从乍浦出发赴日;道光二十六年(1846)“午四号”又运去《红楼梦》散套两部两套。
日本学者大庭脩发现,从1714年至1855年的百余年里,从乍浦港出海,到达长崎港的中国书籍有6118种57240余册。《乍浦集咏》第一次刊印时,就被海商带了24部到长崎出售。当时,每当中国商船到达长崎港,就会有日本收藏家、书商派人打听有没有新书问世。
可以说,《红楼梦》出乍浦,正是乍浦海上贸易发达、文化交流繁盛开出的一朵“繁花”。
你看,沈衡专门写有《海上竹枝词》,可一睹彼时的盛况:
城中几日送梅雨,
海上连朝舶趠风。
报说洋船齐进口,
便开官局看称铜。
海港通天下

《长崎贸易图册》中国商品到达港口的场景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红楼梦》的世界之行为何开始于乍浦?
当然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因。
满清入关,伴随贸易一起绽放的是中外文化交流之花。当时,东亚、东南亚,特别是日本对中华文化倍加推崇,书籍成为重要商品。经济发展、货币流通量增大,铸币需要的铜不少来自日本。
当时,乍浦坐享杭州湾北岸,走海路,可乘季风,逐洋流,南下西洋,北达东洋,往东可直达台湾等地;若走内陆,可沿大运河,北上涿郡,南下余杭,是海河联运的“浙西咽喉”。
所以,1667年,登基六年的康熙,特许乍浦港为与日本长崎港的通商口岸,收复台湾后,他又大开海禁,设江、浙、闽、粤海关,独具地利优势的乍浦自然仍居其中。
嘉兴人文荟萃,文风鼎盛。其所居浙西之地,在红楼出海之时,已有深厚的红学传统,有“红学始盛于浙西”之说。海宁藏书家周春在红楼出海次年,就完成了《阅红楼梦随笔》,这是迄今可考的最早一部《红楼梦》评论专著。
南船北上,北船南下,如百川汇流于乍浦。乍浦港的繁盛由来已久。
早在宋淳祐六年(1246),乍浦已开埠。不过,南宋时,乍浦主要还是拱卫京师的军事港口,虽已“通互市”,但直到元代才成为重要的外贸海港。“元通海道,番舶骈集”,甚至最终取代澉浦成为杭州湾北部最重要的港口。清代,乍浦港已在日清贸易中独占鳌头,“大舶驾风通日本”。
不过,若论海上贸易,乍浦港却是嘉兴境内最年轻的港口之一。
嘉兴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海外交流、往来贸易历史悠久。
据市志记载,三国时,孙权曾在吴淞江口造艨艟巨船青龙舰航海;西晋光熙初,相传海盐澉浦曾有毛人三集洲上,“居民贸易,遂成聚落”,后来,渐渐“人烟极盛,专通番舶”。唐代澉浦、青龙港一带相传也有海贸活动。南宋成书的《澉水志》记载了一则“望夫石”的故事,有海商出海不归,其妻苦盼,化而为石。望夫石在永安湖(今南北湖)仰天坞之右。或许,这可作为澉浦在唐代或者宋代以前已有海外贸易的旁证。
五代吴越国时,有许多实力派商人,拥有私人船队,最著名的是嘉兴人蒋承勋,曾多次往返日本贸易,936年,作为吴越国正式使节赴日。
宋人南渡,赵宋政权对北方失去控制,开始将目光对准海外,开启中国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
他们在地方和港口设立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类似于现在的海关。当时,全国设市舶司及市舶务的有11个地方,其中华亭、青龙、上海和澉浦四处都在嘉兴辖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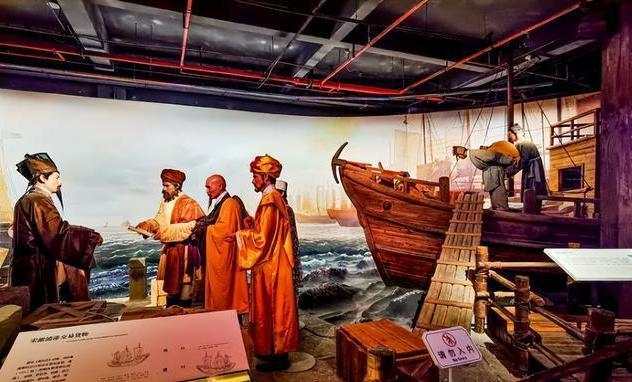
宋代澉浦贸易场景
澉浦是东南沿海最古老的港口之一。
澉浦有“唐建镇、宋通商、元兴曲、明筑城”的说法,澉浦于唐代建镇,宋淳祐六年(1246),澉浦设市舶官,四年后,设市舶场。
当时,大食、阇婆、占城、三佛齐等海外诸国和地区的商人往来于澉浦港口,瓷器、香料、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玳瑁、玛瑙、水晶等成为商贸的“主力”。
南宋时,澉浦作为都城临安的外港,特别是绍熙年间,更是全权接待到杭州的海外船舶。这里海路“东达泉潮,西通交广,南对会稽,北接江阴许浦”,“远彻化外”。商舶云集,甲于诸方,非常繁盛,当地人喜欢奢侈的亭台楼阁,他们接待海南诸货,贩运到浙西各地,当时被称为“商旅阜通”。到元代时,澉浦仍是“招商云集,不减前朝”,是全国七个市舶司之一,“番舶皆萃于此”,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到过澉浦,在游记中记录了澉浦的繁荣,“有极良的港口,有很多很大的船,从印度及别的地方装载巨量的宝贵货物来到这港,京师和这港口有一河相连,船舰可以上溯到这城和更远的地方。”
元初,澉浦和乍浦两港在同一县境,港区相连,澉浦“番舶萃焉”,“东北抵乍浦,商舶间至”。
起先,澉浦港是“优等生”,后来,乍浦港居上,取代澉浦港。因海岸与江口岸线的退缩、海侵加剧,港口淤塞,加上战火荼毒,澉浦港最终在明代海禁中日渐老去。
上海,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建城之前曾是嘉兴辖内小镇,如今的集装箱吞吐量世界第一的上海港肇始于古时嘉兴辖内的青龙港。
宋代以前,青龙江浩瀚无比,贡使商船,会集于此。青龙镇初建于北宋淳化二年(991),地处吴淞江入海口,彼时,浩浩汤汤,“深广可抵千浦”,入海处称作华亭海,来往的船只一直可以行驶到青龙镇旁。北宋文人应熙曾记载,“控江而淮辐辏,连海而闽楚交通”,可见,当时的青龙港主要有内河和南洋两条航路,是这块地域内重要的中转港。
南宋时,青龙港的对外贸易繁盛,“龙舟为天下之盛,佛阁为天下之雄”,宋代人杨潜《绍熙云间志》称青龙镇是“海商辐辏之所”,人称小杭州。
北宋时专门设置了主管海外贸易的机构。北宋宣和三年(1121),在秀州华亭县设秀州市舶务,南宋绍兴年间,主管两浙路地区外贸的市舶司一度移到华亭,长达30余年。
大约在宋元易代之际,海岸线东移,航道淤塞。在沧海桑田这把“杀猪刀”作用之下,青龙港逐渐衰落。
一花开败一花开,澉浦和乍浦两港如是,青龙与上海两镇亦如是,当青龙镇衰落之后,商业中心转移到华亭县上海镇。
平湖境内的广陈镇,也曾是外贸港口。根据《平湖县志》,元代时“番舶至乍,肆列珍异于此,故曰广陈”,可见广陈得名自当时的商旅番舶云集。其实,早在南宋时画家赵孟坚家居广陈,已有广陈之名,据《嘉兴市志》,大约在唐代,平湖独山东北有海湾,广陈濒海,成为商港。沧海桑田,海湾淤为沙地,广陈港也就衰亡了。
航海有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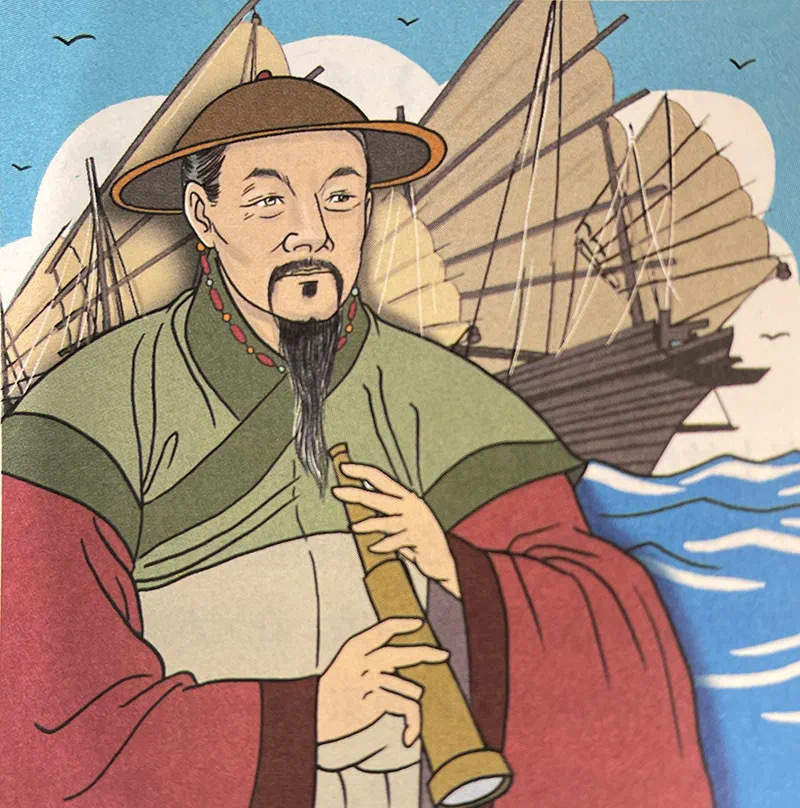
杨枢 李泽峰绘
中国最著名的航海家莫过于七下西洋的郑和。实际上,早在郑和之前111年,元大德五年(1301),嘉兴人杨枢就开启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越洋远航。
杨枢出身澉浦杨氏,这是一个航海世家。
澉浦,东临大海,南连钱塘江,北负太湖,大运河贯穿境内,江、湖、河交汇,自古以来,就是一处海运发达之地。
元世祖拿下浙、闽之地,在泉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四地设市舶司,元至元十四年(1277),杨发成为两浙市舶总司事,督理庆元、上海、澉浦三处市舶司。
杨家很快搬到人杰地灵的澉浦定居。四年后,这里已是商贸云集之地。
帆船林立,码头挤满了南来北往的商贾船舶。他们中的不少人只得停靠在周边村镇,金家桥“客旅巨舟重贩者,多在此泊,入镇贸易复归解缆”;六里堰市,“客舟不能达澉,咸泊于此,居民辐辏成市,木商、鹾贾便萃集焉”。澉浦港成为元朝政府设立市舶司的全国四大贸易港口之一,元代周达观曾描述当时的澉浦港海外贸易,“远涉诸番”,可达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地,“近通福广”,在闽、广之间。
澉浦的发展从大处说,归功于国家政策、地理优势以及造船技术的发展,从小处说,离不开杨氏家族的一次次的远航、兢兢业业的经营。
杨氏在宋代就从事海上贸易,先被南宋招安,后又入元。
澉浦杨氏从杨发开始,开启海上传奇,杨氏子弟世代为官、经商,组成庞大的海上贸易矩阵。
杨发之后,他的儿子杨梓被封为海道运粮都漕万户,后成为浙西宣慰使,继续扩充着杨氏海上贸易版图。
建市场、街道、店房,杨梓在澉浦为商人打造居住、行商的良好环境。每当开市,挂在惮悦寺钟楼的大钟就会敲响,这是他用日本铜铸造的,重达五千余斤,一时成为澉浦盛景。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元兵南征爪哇(今属印度尼西亚),杨梓因熟悉海上事务,被任命为宣慰司官,随军导航。凯旋后,被封为安抚总司,后又任杭州路总管。
杨枢是杨梓之子。元大德五年(1301),年仅19岁的杨枢成为官本船代理人,赴印度洋进行海外贸易。返航时,在波斯湾巧遇波斯使臣那怀。那怀在觐见元成宗时,请求乘杨枢的海船返回波斯。22岁的杨枢,被封为忠显校尉、海运副千户,赐佩带金符,护送那怀回国。大德八年(1304)初冬,他们乘着南去的季风出发了,旅途艰险,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历时三年,才抵达忽鲁模斯港。返航时,杨枢餐风沐雨,又漂泊两年,才完成这次的西洋之旅。
元朝末年,管理松江市舶司的杨枢调集船只,从澉浦港出发,这是杨氏最后一次从浙江向元大都运送军粮。元明易代,明前、中期实行的海禁政策,从根本上断绝航海家族的发展之路,杨氏家族等大批浙西富民被朱元璋迁到他的家乡凤阳。
澉浦杨氏的海上传奇至此消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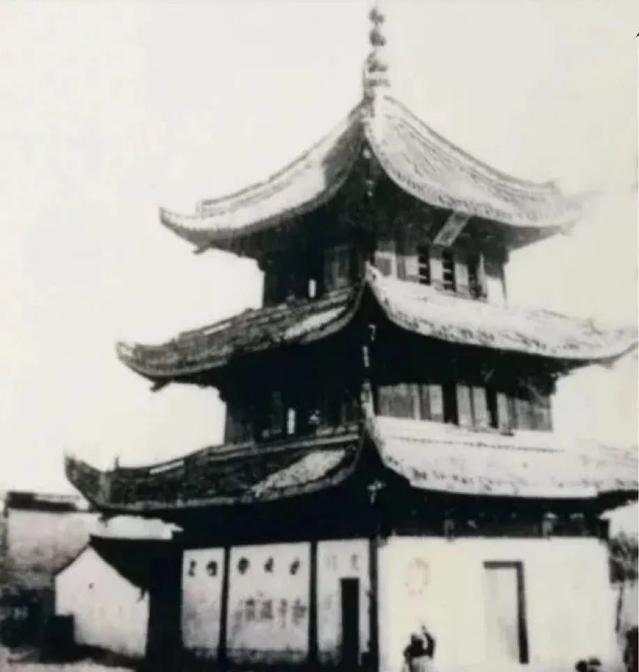
旧时澉浦钟楼
杨发、杨梓、杨枢三代人在澉浦筑室引商,贸易成集,成为巨富。杨氏不仅是影响澉浦、促进中国航海事业发展的航海世家,也是影响一地文化的文化世家。杨家客商仕宦、文人墨客高朋满座,杨梓与著名散曲家贯云石关系匪浅,成为“海盐腔”奠基人。
澉浦北小街吴家角内有著名的荷花池。据载,荷花池开掘于元代,是望族“大船吴”花园中的池塘。“元四家”之一的吴镇,他的祖父吴泽、父亲吴禾,在澉浦从事海运时就住在这里。
义门吴氏是嘉兴最早的航海家族之一。吴泽曾是南宋官员,宋亡后不仕元,归隐嘉兴,打下吴氏航海的基础。吴禾是他的长子,随父航海,号称“大船吴”。吴氏家族航海事业,就如荷花池筑起的亭台楼阁,“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清荷,兴盛蓬勃。吴禾侄子吴汉英承继祖业,少年时便跟随祖父、大伯航海。他的兄弟们也与海上贸易密不可分,黄玠曾有《送吴季良海运歌》,吴季良便是吴汉英的四弟,他的三弟吴汉杰,在元泰定元年(1324)已是温台等处海运副千户,继承了家族的海运事业。
明清之际,乍浦也有从事海上贸易的航海家族。明初,郑和下西洋之后,他的部下及子孙有不少迁徙至乍浦,如齐斌、陶九、沈瘦几等,都曾随郑和漂洋过海到过西洋。谢三定在暹罗、交趾诸国做生意,“以智略为其王大臣所重,与为布衣交,每舶舟抽分之额独宽”,走出国门以后,他仍是著名商人,他的儿子谢崑原承继父辈之志,往来于中日之间。
当时,造巨舰出洋贸易,是不少乍浦巨富家族累积财富的主要途径。明末,乍浦形成陈氏、谢氏、林氏等亲邻相携、患难与共的海外贸易集团。又因乍浦的发展,各地商人汇聚而来,徽、晋等大商人集团云集。
晋商范毓馪与其子侄范清洪、范清注代表的范氏是官商,主持贩铜贸易,成为巨富。乾隆十四年开始,购铜额定为十五船,范氏领帮办三船,剩下十二船民商自办,称“十二额商”。范清洪、范清注等在长崎是中国官民商代表人物,被日本人称为“商人头”。
除此,刘光晟、钱鸣萃父子、两淮盐商王履阶以及吴氏、沈氏、钱氏、杨氏等巨商也是盛极一时的航海家族。
舟楫为马,江海可渡。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攥一把历经千古磨砺的细沙,渺沧海之一粟,羡海天之无穷,和浪花一起成长的嘉兴,流淌着一个个出海的故事,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燃起一盏盏明灯,向更遥远世界连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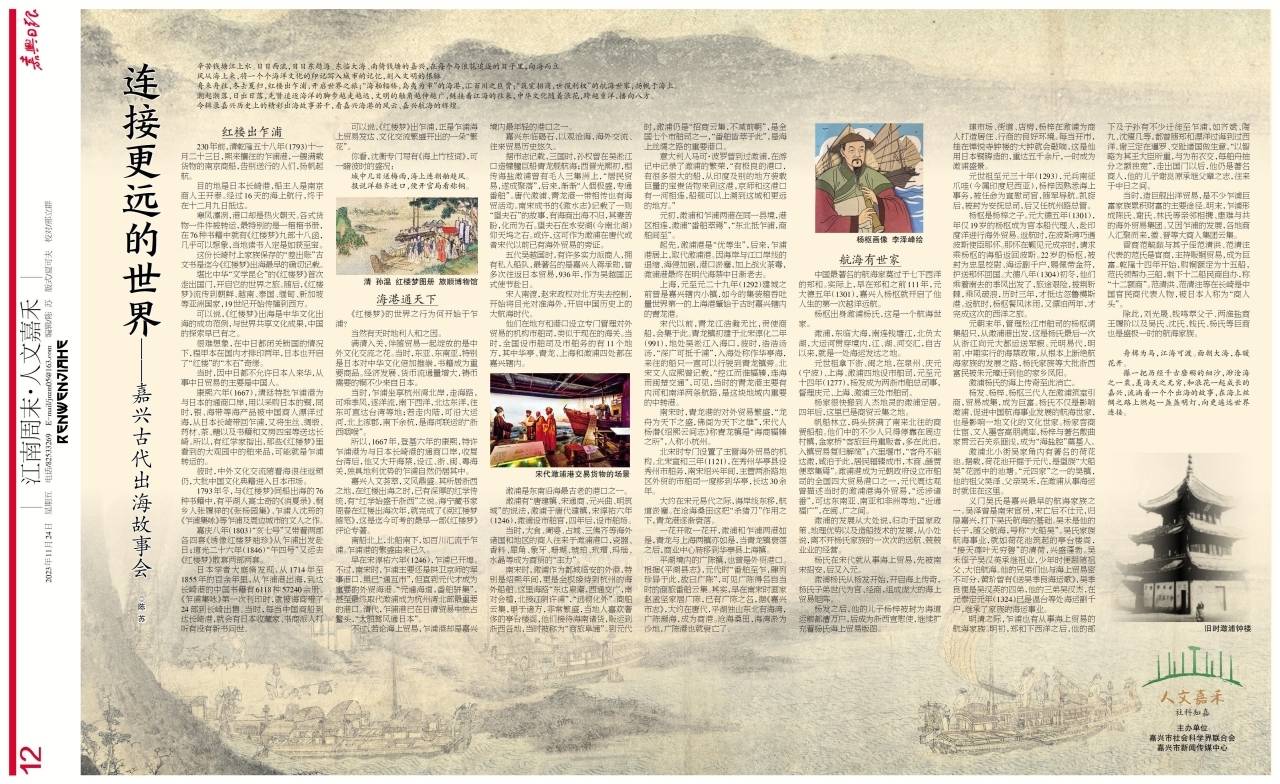
《嘉兴日报·江南周末》人文嘉禾2023年11月24日报道

编辑:陈苏
海报:陈苏
责编:戴群
审核:邓钰路






独家视角 读嘉呈现

